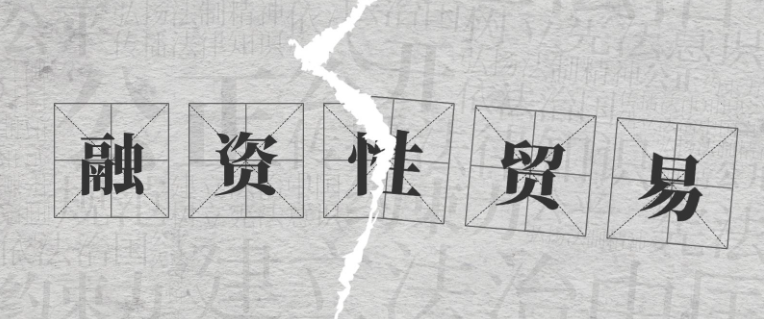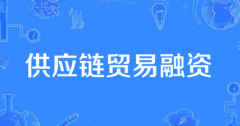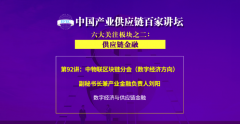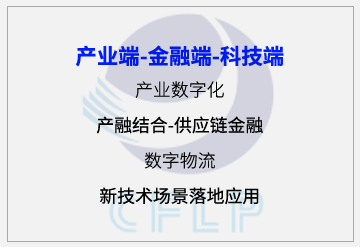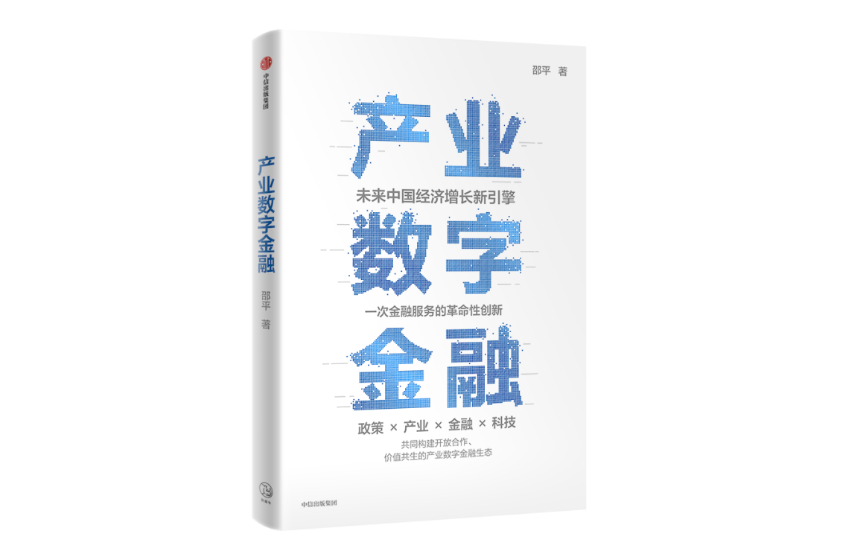“名保實貸”下,保理人如何要求擔保人承擔責任?最高法典型案例研判

編者按
保理變借貸,擔保人責任如何定?本團隊結合最高法典型司法判例,詳細分析“名為保理,實為借貸”中擔保人在不同情形下的責任承擔義務之范圍,為保理公司業務開展及商業決策提供專業法律指引。
裁判要旨
保理法律關系以應收賬款轉讓為前提,保理申請人未提交《應收賬款確認函》不構成保理法律關系,兩者為借貸法律關系,旨為保理合同提供擔保的擔保人無需繼續承擔擔保責任。
案情簡介
一、2018年12月17日,T公司將其對某科技公司的應收賬款轉讓給H銀行,辦理無追索權保理業務,雙方簽署了《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及補充協議(以下合稱“《保理合同》”)。
二、H銀行與T公司簽訂《銀行承兌協議》作為《保理合同》項下融資合同,H銀行同意承兌以T公司為出票人的匯票,承兌了33張出票人為T公司、收款人為天津某科技公司的銀行承兌匯票。
三、H銀行與Q集團簽訂《質押合同》,約定Q集團以定期存單為《銀行承兌協議》項下的債權提供質押擔保。
四、2019年12月6日,因上述銀行承兌匯票被提示付款,H銀行為T公司墊款共計30630萬元。
裁判要點
一審法院認為,保理業務開展以受讓應收賬款為前提,自T公司向H銀行提交《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起,但T公司未提交,故H銀行未取得案涉應收賬款及相關權利,兩者不構成保理法律關系,僅為一般借款合同關系。
對于《質押合同》,法院認為H銀行審查了授權代表的授權文件、擔保決議的出具是否符合章程規定,已履行了形式審查義務,故案涉《質押合同》合法有效。
二審法院認為,《銀行承兌協議》為《質押合同》的主合同,為保理合同項下的融資合同,《質押合同》實際意在為保理業務所形成的債權提供擔保。現因H銀行擅自對保理合同的履行內容進行了變更使保理法律關系變為借貸法律關系,違背了Q集團提供擔保的本意,加重了Q集團實際承擔擔保責任的風險,且上述變更合同履行方式并沒有取得Q集團的書面同意,故Q集團無須承擔擔保責任。
實務經驗總結
根據《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條的規定,擔保合同是主債權債務合同的從合同。主債權債務合同無效的,擔保合同也無效,除非法律另有規定。這意味著,如果主合同被認定為無效,擔保合同通常也會被認定為無效。所以在本案中,最高法認為,當主合同發生變更,特別是當主合同發生實質性變更時,原債權債務關系消滅,新的債權債務關系產生,擔保責任隨原債權債務關系消滅而消滅,擔保人不再承擔擔保責任。
合同內容的變更通常是通過變更合同的條款內容來實現的,而合同的條款通常有主要條款和非主要條款。主要條款一般包括以下條款:標的、數量、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期限、地點和方式、違約責任和解決爭議的方法。這些條款涉及當事人的主要權利義務。非主要條款是指與當事人的主要權利義務無關或者影響不大的,諸如幣種、運輸方式、通知方式等等。非主要條款的變更無需經過擔保人的同意,且若如果主要條款的變更導致主合同的責任的范圍是可預見的,擔保人的擔保責任在此也可以確定的,如借款合同的借款數額,則這些條款的變更也無需擔保人同意,只需要將擔保人的責任限制于原有的范圍,而無需免除其擔保責任。但若主合同的條款變更導致的合同責任范圍無法預見,擔保人的責任也無從確定,此時從保護擔保人利益的角度而言,應該要求主合同的變更應該經過擔保人的同意。如保理合同變為借款合同,此時整個合同性質發生了變化,應該認為原主合同發生了消滅,擔保人由此免除擔保責任。
但是否出現“名保實貸”時,保理人必然無法要求擔保人承擔責任了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當主合同無效時,擔保人不是必然無須承擔責任的,以下為一些常見的特殊情形:
1.擔保人明知合同性質:擔保人在簽訂擔保合同時,如果擔保人知道或應當知道保理合同實質上是借貸關系,且保理合同因此被認定為無效,擔保人可能無法主張擔保合同無效。例如(2020)最高法民終537號判決中,最高法認為“案涉合同無效后依據合同法第五十八條形成的債權債務為當事人明知的基礎法律關系。當事人為實現這一真實發生的債權債務而訂立的還款協議及擔保協議等,應當認定為有效。”(2021)最高法民申4861號裁定維持了這一觀點。
2.擔保人對于擔保合同無效存在過錯:如果擔保合同無效,擔保人通常需要對保理合同(即主合同)的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查,若其未對保理合同進行審查導致合同無效,并最終導致擔保合同無效的,需承擔部分責任。根據《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十七條的規定,主合同無效導致第三人提供的擔保合同無效,擔保人無過錯的,不承擔賠償責任;擔保人有過錯的,其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的三分之一。
3.金融機構獨立保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獨立保函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即使主合同無效,獨立保函仍然可能有效。這是因為獨立保函具有獨立性,其效力不依賴于主合同。考慮到金融機構的獨立保函,保理公司開展保理業務時,除了考慮一般商事主體提供擔保的,也可以考慮要求申請人提供金融機構的獨立保函。
綜上所述,當保理合同無效時,擔保協議不必然無效,仍然存在保理人可以要求擔保人承擔責任的情形,當然這需要考慮擔保合同的效力、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及其他特殊約定等要素。
法院判決
圍繞上述爭議焦點,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審審查中的“本院認為”部分進行如下論述:
根據本院查明的事實,三份《質押合同》中約定Q集團所擔保的主債權為債務人在H銀行辦理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所形成的債權,《銀行承兌協議》亦明確約定本協議系《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項下融資合同,銀行承兌匯票由H銀行作為最終承兌人并承擔相關付款責任,T公司無需再向H銀行支付銀行承兌匯票兌付資金。因此,Q集團系就《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承擔擔保責任,《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可以視為《質押合同》的主合同,Q集團作為出質人,其承擔擔保責任的本意是在H銀行依照《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履行受讓T公司對某科技公司應收賬款的前提下,對某科技公司未能按時付款所承擔的擔保責任。上述關于《質押合同》《銀行承兌協議》《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間關系的認定,符合當事人之間合同的約定。
本案中,按照《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第5.1.2、5.2、5.3.2、5.5條的約定,H銀行在為T公司提供保理融資服務前,應當收取并審查T公司提供的《應收賬款轉讓明細表》、發票、貨運證明、質檢證明及其他證明商務合同項下的交貨義務確已履行的文件以及《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是權益轉讓的標志,自T公司提交確認的《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起,T公司將其商務合同項下享有的應收賬款轉讓給H銀行,T公司所享有的與應收賬款相關的一切權利、權益同時轉讓給H銀行。即H銀行向T公司提供保理融資服務是以受讓T公司應收賬款為前提的。然而,H銀行在實際履行《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的過程中,并未按照約定的內容履行,而是擅自進行了變更,其在未收到《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及部分發票、證明的情況下,即為T公司開具銀行承兌匯票,提供了保理融資服務。T公司在獲得融資款后,即不再向H銀行交付《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等證明及文件資料,經原審法院向T公司釋明應依約向H銀行提供上述材料后,T公司在指定期限內仍未提交。正是由于H銀行擅自變更了合同約定的履行方式,放棄了雙方預先設置的“先受讓應收賬款,再提供融資服務”的風險防控手段,放任風險的發生,導致以后T公司拒不交付《應收賬款轉讓確認函》,進而致使H銀行未成功受讓案涉應收賬款及相關權利。H銀行在履行過程中將保理合同事實上變成了一般借款合同,導致了其提供的融資款無法追回的結果。H銀行對主合同的變更履行,使得H銀行與T公司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由保理關系改變為一般借款關系,從而導致債務人、擔保責任的范圍等質押合同的基本內容均發生了根本變更,Q集團將被要求就因H銀行提前提供保理融資服務、T公司無法償還承兌匯票墊款而產生的一般借款合同債務承擔擔保責任。這一變更不僅違背了Q集團提供擔保的本意,而且在客觀上可能極大地加重Q集團實際承擔擔保責任的風險。再考慮到若H銀行按照約定的方式正常履行《無追索權國內保理業務合同》,本案的糾紛可能實際上不會發生,而H銀行變更合同履行方式并沒有取得擔保人Q集團的書面同意,故Q集團無須承擔擔保責任,H銀行應就其提前提供保理融資服務所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擔責任。
案件來源
(2020)最高法民終907號、(2021)最高法民申2226號
文章來源:保理法律研究,作者:林思明/駱凱,圖片來源:網絡。
本文已標注來源和出處,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煩請聯系我們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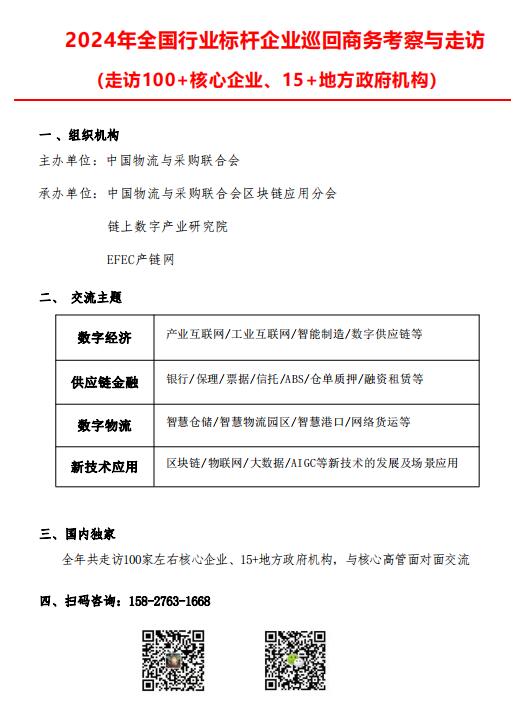
上一篇:票據貼現如何深化支持實體經濟
下一篇:供應鏈服務+金融從業者必懂:120個供應鏈服務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