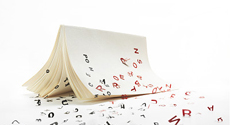硅谷高科技專家王維嘉:目前人工智能不適合無人駕駛
【EFEC導讀】人工智能未來會影響哪些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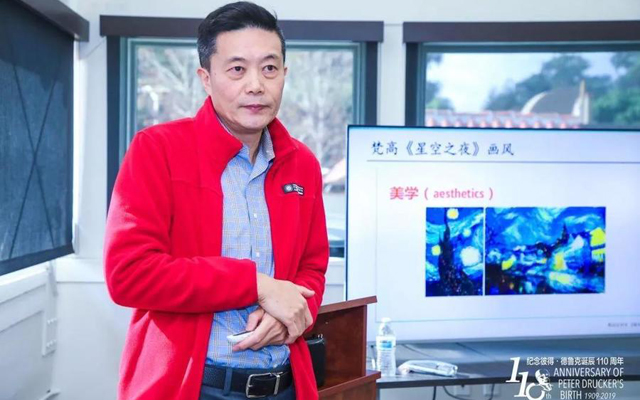
編者按
11月29日,美國舊金山,“重走德魯克之路”游學課堂邀請到硅谷著名高科技專家、《暗知識》作者、硅谷風險投資公司AimTop Ventures創始管理合伙人王維嘉先生結合自己的新著《暗知識》,為企業家學員們分享人工智能的本質和相關的創業投資機遇,深刻的洞察和精彩的觀點讓學員們受益匪淺,許多學員感嘆“終于有專家把人工智能講清楚了。”
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的區別
人工智能和互聯網行業有什么區別?最重要的區別是一個是2C的生意,一個是2B的生意。
我的好朋友李開復在他的書里說未來的人工智能是中美兩國領跑,其他國家遠遠地甩在后面。但這個結論完全不對,原因就是2B。比如一個法國核電廠要做人工智能改造,是法國的公司能拿到這個單,還是美國公司能拿到?當然是法國,因為2B生意的進入壁壘非常高,2C是沒有進入壁壘的。
比如抖音現在全世界非常普遍,谷歌、Facebook就不用說了,用戶沒法控制,只要覺得好就會用。所以開復這個判斷是錯的,我覺得是把互聯網時代的思維拿到了人工智能上。
在互聯網時代為有一個規律叫贏者通吃,但2B的生意完全沒有。中國有300多家公司人臉識別公司,頭部的大公司就4-5家,各家都不一樣。所以2B的生意和2C的生意完全不一樣。

硅谷著名高科技專家、《暗知識》作者王維嘉
人工智能未來會影響哪些行業?
可以用三個標準判斷人工智能(AI)是否對一個行業有影響:
第一,這個行業本身會產生大量的生產或者服務數據。如果不產生數據人工智能就無用武之地。
第二,數據要足夠豐富和復雜,比如放一個空氣凈化器把它的聲音都記錄下來,這也是數據,但這個數據沒有用,非常單調。
第三,行業要有錢,如果行業沒錢,沒人愿意投資來顛覆你這個行業。
如果用這三個標準就很容易判斷了,第一就是金融行業,這三個標準絕對滿足,所以今天的金融行業全面地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不論是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理財都一樣。
但人工智能的創業公司在銀行業會遇到一個問題,你可以跑到豬場去蹲點讓人工智能學會刷豬臉,豬臉這樣的數據你隨便看,但銀行不可能把自己的數據放出來,因為這是它的核心商業機密。
所以今天金融業比如平安保險,現在已經有一個500人的博士團隊自己做人工智能,所有的大金融公司全都在自己做。小公司根本進不去,最多他說你來教我技術,教完了以后還是自己做。
但醫療的圖像就沒問題,對醫院來講,比如X光片你放到大街上沒人知道這是誰的肺片,這些東西不是醫院核心商業機密,所以愿意放出去。
今天在中國我比較看好醫療圖像方面的應用,因為中國現在要大力普及普惠醫療,現在鎮一級的醫院都能買得起X光機。如果機器能比醫生看得更準,問題就能大大解決,像這樣的應用就非常有希望。
人工智能在制藥領域的應用
全球制藥市場每年有1萬億美金,其中5000億是小分子藥。它的基本原理很簡單,比如導致肝癌的原因可能是某個目標蛋白質,科學家找到一個小分子化合物卡在目標蛋白里面,放在它的縫里把它抑制住,這個病就治好了。
過去尋找的方式是給科學家一個目標蛋白質以后,大藥廠的幾百位化學家就從數據庫里試,和愛迪生試鎢絲的過程一模一樣。他們完全憑著經驗去猜然后做大量的測試,但大部分化合物分子和蛋白質是不發生任何反應的,只能不停的更換。
這個過程大概需要2-3年的時間。如果在美國,需要同時雇兩到三百位化學家,每人每年25萬至30萬美金工資,花費幾億美金才能做成。
但這家公司把歷史上所有成功配對的信息全部交給機器學一遍。如果蛋白質長這樣,就給它配一個這樣的化合物,如果蛋白質長另外那樣,就給它配另外一個化合物,還是前面機器學習訓練的過程。
這個過程特別像紅娘,如果之前已經成功地配了100對婚姻,現在是第101對,你給我個姑娘想找個小伙,基本根據經驗我就知道什么樣的小伙是適合的,因為已經有了很多經驗。
所以這個機器做的事和紅娘沒有任何差別,只不過它看到的配對是幾百萬個,它看的小伙子是蛋白質,姑娘是小分子化合物。
所以這個特別適合人工智能,因為它倆配對就是相關性,看多了就知道下一對相關性怎么回事了,今天它是全世界這個領域里做得最好的一家公司。
目前人工智能不適合無人駕駛
過去自動駕駛是我最感興趣的一個領域,我大概看了20-30家自動駕駛軟件公司。如果真正能做到無人駕駛的話,這對于行業的顛覆是史無前例的,甚至都不需要停車場了,也不需要買車了。
但我們一家都沒有投,因為我得出一個結論,自動駕駛是一個特別不適合神經網絡做的事。
今天全世界做自動駕駛最牛的公司是谷歌,谷歌從2009年開始做,現在每年大概花40-50億美金,2000位博士,它的汽車已經大概行駛了10億英里,天天在外面跑。
今天的自動駕駛是把每一個駕駛場景當成一幅圖像:這幅圖像有3個老人、1個小孩、1棵樹、1輛車該怎么處理?這幅圖像有1個自行車、1輛汽車,該怎么處理?
它駕駛幾十億英里的目的是企圖把全世界所有駕駛場景都經歷一遍,這可能嗎?
想想我們人類駕駛,你看見前面有3個小孩或者2個小孩,每個場景不是提取它的相關性,而是理解場景中每個物體間的邏輯關系。
今天的人工智能完全沒能力做這個,只是提取相關性。
所以駕駛是讓機器做一件“人很容易做,但機器非常難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結論是像谷歌這樣把方向盤去掉的無人駕駛,10年內根本做不到。對于我們風險投資來講,10年內做不到就是砸錢的,所以我們到現在一家都沒有投。
現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家自動駕駛公司,我覺得至少90家要關門,剩下10家轉型,在很多封閉環境和有限場景依然可以做,比如廠區、校園、倉庫、海港這些地方。有限場景就那么多東西,比如在港口撞車了,就是撞壞貨而已,不會死人,在這些條件下無人駕駛是可行的。
至于乘用車,只能一點點增加功能讓人的駕駛更舒適,更安全,而無法取代人。這是我們根據對技術的深入了解做出的判斷。
人臉識別的問題不在技術
人臉識別非常適合人工智能,比如想抓一個壞人,在街上照了一張照片,到數據庫里對比到底他是誰,這完全是相關性,它做得快而且比人要識別得更準確。

圖片來源:領教工坊
但人臉識別的市場是有問題的,它的問題不在于技術,因為進入門坎太低。
在美國根本沒市場,在歐洲更沒有市場,只有在中國的應用市場是巨大的。因為每座城市政府、每個公安局都希望借助這個系統維護社會治安,中國現在的公共場所已經有4億個攝像頭了,未來至少要翻一倍,市場非常大。
但中國的人臉識別已經是紅海了,目前人臉識別背后的芯片還是英偉達、英特爾的芯片,算法還是谷歌的算法,除了極少數的幾家公司有一點自己的算法,絕大多數,至少300家人臉識別公司都是雷同的算法。因為技術差不多,最后就是拼關系。
人臉識別潛在的安全隱患
今天對人工智能最大的一個擔心不是人工智能會控制我們,這還早著呢,基本不可能,目前連無人駕駛都還做不到。但個人隱私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銀行帳號都是用人臉來開的,我的臉就是我的密碼,走在街上,我的密碼就一直在被廣播,隱私是非常大的問題,但今天沒有人去關心。
我覺得中國今天既然是全世界人臉識別最先進的國家,也應該在個人隱私保護上做成最嚴密的,因為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否則一定會出很大的問題,只是今天還沒有出事。
人類永遠無法做到的群體學習和光速復制
我用了“意外”這個詞來描述人工智能未來的應用,因為很多應用我們今天可能還看不到。
比如iPhone剛問世的時候在中國引起了一場爭論:“移動互聯網是PC互聯網的延伸還是全新的?”當時有兩派,一派以李彥宏為首,把百度搜索條放在手機上面等于多了一塊屏幕,從百度角度想確實是那么回事。
另一派覺得這是一個全新的東西,當然我屬于另外一派。
雖然沒人知道是什么東西,但我們知道手機和PC的區別是:第一,它永遠在我身上,第二,它有位置信息。未來的應用一定和這兩件事有關,果然今天使用微信是因為它老在我身上,今天使用滴滴打車是因為有位置信息,但當時你是看不到的,只是覺得這東西確實和PC不一樣。
今天還不知道人工智能未來會有什么讓我們非常吃驚的東西,但我知道有一點是和群體學習、光速復制的能力相關。
我舉個機械手實驗的例子,谷歌讓機械手自己學習把雜物從盤子里一個個抓出來。雜物有各種不同的形狀,機器一開始亂抓,經過15天的摸索,它自己就學會了。
緊接著他們做了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實驗,把15臺機器用網絡連起來,讓每一臺都做一樣的事,還是從頭學起,但學習時間變成了一天。因為這15臺機器都在亂摸,突然有一臺機器抓到東西了,它馬上告訴其他機器到哪里能抓到東西。
這相當于我們人類看到這樣一幅場景,有1萬個孩子在一個大操場上學騎自行車,大家一開始全在摔跤。突然間有個小姑娘學會騎了,與此同時剩下9999個全都會騎了。
這是因為機器間的神經元連接可以取出來復制到其他機器里去。也就是說未來在全球范圍內,甚至在星系的范圍內都可以做出這種高度協調的東西,當然有光速的延遲,但至少在幾百平方公里可以實現。
這對未來的戰爭,大量的協同、合作、生產是有本質性影響的,也是我們人類永遠做不到的。
人工智能是個偏科生
人工智能在藝術上也有很多應用,比如給機器看很多梵高的畫,它就可以把一張丹麥的照片畫成一幅梵高風格的圖畫。
我們人類就完全沒有可能學會這樣的筆觸和顏色。因為機器可以同時處理幾百,甚至上千、上萬個變量和非常復雜的相關性,我們人類只能處理三個。
所以只要是在處理復雜變量、復雜相關性的地方機器一定會遠遠超過人,但一旦到理解邏輯關系和因果關系,機器就傻眼了。至于到了情感,機器就徹底沒戲了。
我寫書的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要給人工智能劃出個邊界,到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不是說:“哇,機器時代來了,我們人類都要被奴役了。”那是完全不懂。典型的代表就是寫《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他后面幾本書對人工智能一點都不懂,完全是在瞎寫。
還有一類說人工智能什么用都沒有。其實不是,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有非常神奇的應用,但它有點像一個偏科的學生。雖然神經網絡是模仿人腦的,但之所以它能比人腦快,能夠做我們人腦做不了的事情是因為:
第一,快。人腦的神經元每秒鐘只能開關200次,但因為機器是芯片,它可以每秒開關10億次,比人腦快了500萬倍。我們從腦子發出信號的傳輸速度是每秒鐘120米,但在芯片里傳輸速度是光速,它的傳輸速度和計算速度都是我們的幾百萬倍。
第二,準。現在我說10個數字,可能大多數人只能記住一半的數字,剩下的就忘了。因為人腦是非常不可靠的東西。但你現在下載一個1G的電影,一個比特都不會出錯。如果錯一個比特程序就不工作了,機器可以記得非常準。
第三,可復制,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機器腦袋里的知識是可以復制到其他機器的,但人不可以。
機器能夠做出非常神奇的事情,但它仍然很笨,不能舉一反三,駕駛要把每個場景當成一幅圖像來處理,沒有符號,沒有情感,沒有意識。所以我把今天的人工智能叫做:“智商偏科、情商為零。”
馬云說的對不對?
馬云前兩年說大數據、人工智能讓我們可能回到一種新的計劃經濟,這遭到一線經濟學家的痛斥,我現在從一個企業家的角度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馬云說的對不對。
大家知道市場有供給和需求,如果是一個已知需求的市場,比如礦泉水的消耗量,你能把它的信息收集得非常準確的話,確實很有用。
馬云說:“我對于你老婆的消費習慣比你還熟悉。”剁手黨天天在他那兒買東西,他肯定比你熟悉。
美國就出了這么一件事,塔吉特公司有天給一位父親寫了一封信:“恭喜你女兒懷孕,我們可以給你提供這些嬰兒產品。”結果父親非常憤怒,他女兒才上初中就亂發這種東西,寫了一封信抗議。塔吉特說不好意思,因為你女兒在我們的網站上瀏覽的信息一般都是孕婦才會看的東西。結果她爸一問,女兒果然懷孕了。塔吉特比她爸更早知道他女兒懷孕。
過去哈耶克不是說信息不能收集嗎?馬云說我現在可以收集了,既然收集就可以集中,既然可以集中就可以計劃了。
如果是一個已知的需求,他說的確實不錯。但即使在一個存量市場,產品永遠可以不斷改進,比如礦泉水的瓶子可以更時尚。所以即使在一個已知市場,它的供給方的信息仍然藏在企業家腦子里,仍然沒有辦法集中搜集。
至于未知的需求就更不用說了,喬布斯說我的市場調查就是每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對著鏡子看自己。當然他這是開玩笑的,iPhone是2007年出來的,如果2006年他跑到中國大街上拉著一個人說,你覺得一個智能手機應該有什么功能?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上來。
過去20年不知道多少家公司想做掌上電腦的都失敗了,虧得血本無歸,但蘋果一直在嘗試,到2007年的時候所有的技術都成熟了,達到了用戶的基本需求之上。但這個過程經過了無數的試錯和失敗,這些東西在喬布斯的腦子里,你到哪兒去收集這樣的信息?就算你能收集來,誰去做這樣試錯的財務的責任?不知道多少公司都賠了,包括風險投資公司,包括企業家自己。
所以企業家這種創新精神,這種試錯精神是永遠無法被收集的,不管你有多強大的電腦或者多強大的數據都無法收集。
結論就是馬云不是完全說錯了,只是在已知需求的這個市場上,大數據、人工智能有用,在已知的供給上用處不大,在未知的不論是供給和需求市場上都是一點用都沒有。所以只要把市場看成是由供給拉動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就永遠不可能代替企業家精神。
本文已標注來源和出處,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
上一篇:嚴監管加強監管 促融資租賃業回歸本源
下一篇:人民銀行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發生業務量超過900億元